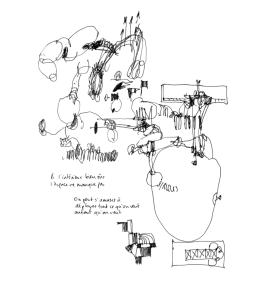
本文是拉康对分析家Catherine Millot女士所提出的一个问题的即兴回答。1974年于当时的Vincennes大学(现在的巴黎八大)的精神分析系Millot向拉康提问:死亡之欲望是在眠之欲望之侧还是醒之欲望之旁?当时拉康沉默地坐于其办公室,半小时过去,当Millot都准备放弃听到该问题的回答之际,拉康为了让Millot可以尽可能地做下笔记,以一种及其详尽的方式给出了回答。以下,就是当时Millot记录的全部内容。
在醒着之外
弗洛伊德所设想的死冲动含有身体的苏醒即是其自身的毁灭的意味,因为在享乐原则的反义层面上,他将此称为一个他处(un au-delà),这个他处,即是一个对立位。
至于生命,其正是完全醒着的他处。生命不被想象,身体则什么也捕捉不到,而仅仅只是承载着生命。当弗洛伊德说:生向往着死,这也是为了生,并作为生的体现,作为生在身体之中渴望着一种完满的意识。我们可以说正是在那里,一种绝对苏醒之中,仍然有一部分的梦是醒着的梦。
我们从未醒来,因为欲望供养着梦境。死亡是一场梦,是一场入到其他的可使生命不朽的梦境,然而这梦仅存于神话之中。死亡正是位于苏醒之旁。若说生命是可以梦想着绝对苏醒的某物,这是绝无可能的。例如,在佛教信仰有关于涅槃的部分中,生命梦想着逃至其本身。然而生命是现实的,这一归返是神话式的也是那些仅自向于语言的梦的一部分。如果没有语言,我们就无法开始梦着作为一种可能性的死亡。这种可能性因在这神话且神秘的向往中而变得更加矛盾,我们重返到通过一种计算而得到的绝对现实(实在)中。
我们梦想着混淆我们所推论出的我们栖息于语言之上这一事实。然而,因为我们栖息于语言之上,我们遵照于一种形式主义,更准确地说是以计算的秩序的形式,我们想象着存在一种实在的绝对符号知识。最终,在涅槃中,我们所渴望的正是沉溺于这毫无迹象的绝对符号知识之中。我们将在这被假设的符号知识所支撑着的世界中迷失,对于每个身体来说,该世界仅仅是一场梦。
终有证据可以证明,唯有语言连接于死亡。这是(本我)被抑制了吗?我们无从确认。可以想像的是整个语言仅是为了不去思考死亡而制作的,因为死亡其实是最无法思考之物。这的确是为了如一个清醒者般去构想死亡,我所谈及的内容涉及了我的波氏结理论(符号界,想象界,实在界)。
我更倾向于认为性与死亡是紧密相连的,正如众所周知的——从性的角度而重构的身体是死亡的主体——所证实的那样。
更确切地说,通过与性毫无关联的抑制,语言否认了死亡。致力于捕捉住性的完全清醒是被拒绝的,但可采用其他形式,性的结果的形式,即是死亡。
实在的无意义
在弗洛伊德构想生命如无机物一般向往着回到粒子惰性的状态[1]时,他犯了一个错误。在身体中的生命仅存活于享乐原则。但在言说者那里的享乐原则是服从于无意识的,即是指语言。语言终究仍是暧昧的:其填补了性别关系的空缺并掩盖了死亡,同时可以如一种深处的欲望般表达出来。然而在动物那里,在语言的相似物中,我们未找到关于死亡意识的证据,但我不认为只有人类对此拥有更多,关于语言的事实:语言谈论着死亡这一现象并不表明其拥有任何关于死亡的知识。
只有通过性的真实(实在)才能触及到那遥远的界限。死亡是一种仍具有梦的特性的清醒,然而这梦是联系于语言的。某些欲望的苏醒表明较之死亡,其与性有着更多的联系。
在言说者那里的梦涉及到ab-sens,这个由无性别关系而构成的实在的无意义,恰恰更激发了解关于这无性别关系的欲望。如果这欲望是缺失的秩序,我们不能认为这是其原因,语言在此层面上尽其所能地尝试去建立关系,甚至给这一关系以记号,但从未成功。语言可以被设想成生长于这无关系的层面之上,然而我们不能说这个关系是存在于语言之外的。◎